
「同題異寫 ‧ 兩種風景」作者團隊由五位背景不同的校友組成。專欄每期設一題目,由兩位作者各出機杼,自由發揮。五人輪流執筆,每次不同組合,期盼刷出寫作的新火花。

本期作者 楊思毅(17 /政治與行政學)
喺香港土生土長嘅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(Complex PTSD)倖存者。二○一二年入新亞後,有幸結交到嚟自五湖四海嘅好朋友、職員同老師,令佢即使跌跌碰碰,都有人互相扶持。臨畢業前,由於一位好朋友自殺身亡,加上家庭同學校嘅童年創傷,令佢對心理、輔導學同情緒教育漸漸產生興趣,後來加入Teach For Hong Kong 喺基層小學教咗一年書,望到唔少學生同佢細個好似,因為屋企同學校冇教,所以唔識講自己感受,影響社交同學習。二○一八年,佢同另外兩位中大校友創立非牟利機構JUST FEEL 感講,希望喺香港學校同家庭推廣「善意溝通」同「社交情緒教育」,凡事「先處理心情,再處理事情」,令每個小朋友成長得更幸福。
問我得失有幾多 其實得失不必清楚
我但求能夠一 一去數清楚。
一提起「得失」,我的腦海浮現出這句歌詞,出自陳麗斯的《問我》,這首七十年代的舊歌。如果黃霑還在生,我會問他為甚麼想「能夠一一去數清楚」。我曾經很渴望數清楚自己的得失。我想其中一大原因是,父母從不讚賞我和姐姐,所以我們從小便拚命尋求外在的認可,追逐名利、獎項。有好一段時間,我會因為很小的「失」而感到非常挫敗、失落,又或會因為各種「得」而感到非常自豪,甚至有點自大。久而久之,我感覺很疲倦,漸漸走到另一個極端,遇上「得」時,就會跟自己說:「這不是甚麼成就,不值得高興!」;遇上「失」時,又會跟自己說:「這沒有甚麼大不了——不應該有這麼強的感覺呢。」我壓抑了自己的感覺,一直強迫自己走下去,甚麼也變得有點麻木……
幸好幾年前,我從「善意溝通」老師Jesse和Catherine那裏學習到「慶祝與哀悼」這個儀式,讓我得以從「麻木」的狀態中走出來。這個儀式的目的是幫助我們與內在真實的情感連結,從而恢復人性(restore humanity)。 [1] 為甚麼要「恢復」呢?因為我們容易受主流文化和教育影響,內化了上述的思考和表達方式,經常不自覺地否定、壓抑了自己和別人的情感,更忽略了這些情感背後的需要,漸漸失去了人性。
那麼「慶祝和哀悼」具體上是甚麼意思呢?根據另一位「善意溝通」老師曹文傑 [2](小曹)的整理,「慶祝」是指在特定事情中與得到滿足的需要連結,而「哀悼」則是指在特定事情中與得不到滿足的需要連結。 [3] 舉例而言,行山時我感到很舒暢、自在,滿足到運動和自然的需要,我就可以「慶祝」。若果突然間,有一隻野狗衝出來吠我,我嚇一跳並心跳加速,感到驚嚇、害怕,未能滿足到安全的需要,我就可以「哀悼」。
然而,在主流文化的影響下,我們有時會因為害怕自己變得苛索、貪得無厭,而不去覺察和擁抱自己的需要,有時又會覺得只能透過命令/壓迫得到我想要的東西,結果往往只得兩個選擇:Push(用威迫、利誘、武力取得想要的事物)和Let go(壓抑或放棄欲求本身)。後者在不少宗教中也有類似的思想。幸好,「善意溝通」結合了「慶祝和哀悼」,為我們開啟了第三條路——「盡情去要而不執取」(Wanting fully without attachment):接納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需要,並放下對特定結果/策略的執取,同時不否定欲求本身。 [4] 我有想過在這裏分享一個自己「盡情去要而不執取」的例子,但因為我也在學習、嘗試實踐這概念中,擔心自己的理解未夠透徹,反而會誤導了大家,原本寫了一段,後來也決定刪除。如果你有興趣了解更多,邀請你一起看這篇原文。 [5]
所以,同樣地,若我們有「得」,可以慶祝;有「失」,就可以哀悼。就如《問我》歌詞中:
無論我有百般對 或者千般錯
全心去承受結果
面對世界一切 那怕會如何
全心保存真的我
那麼,我們透過如實地覺察、接納自己每時每刻的感受和需要,並與他們連結,長遠可以恢復我們的人性,從而有更多內在資源去追尋目標,同時避免讓成敗得失主導我們的思考和決策。就如《問我》歌詞中:
願我一生去到終結 無論歷盡
幾許風波
我仍然能夠講一聲 我係我
嗯,我也在學習容許自己覺察、接納和表達自己的一切情感,無論遇上甚麼人和事,我都希望能真誠地做自己,「盡情去要而不執取」—— 仍然能夠講一聲,我係我。
註:由二○二三年一月開始,我和機構另一共同創辦人郭梓樂,以及小曹一起在和聲書院通識教育課開辦「善意溝通」課程。我相信這是大中華區,甚至是亞洲第一個在大學正式開辦的完整「善意溝通」課程。歡迎各位對「善意溝通」有興趣的朋友與我們交流呢!
( 文/楊思毅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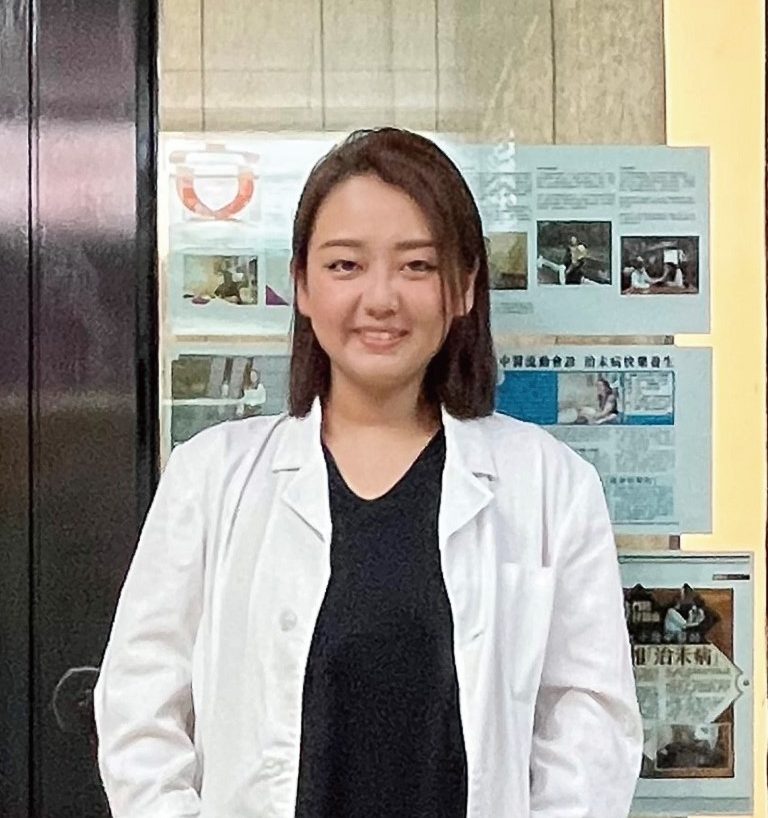
本期作者張瑩(17/中醫)
在學思樓生活了四年。寸心中醫創辦人,平生最大願望是世上再無病人,順理成章結業大吉。致力於推廣正確中醫常識,希望人們都能了解自己身心狀況更多,也懂得在需要的時候求助。現與丈夫及四隻愛貓居於香港,過着忙碌而快活的日子。
本以為經過搬家、診所搬遷、公司擴張,二○二三年所得的已足夠豐富。沒想到到了年末,上天還是給了我這一年最後、也最震撼的一課。
十一月底,愛貓查查突然不思飲食。雖然貓在季節轉換時食慾減退是常有的事,但在愛吃的查查身上出現這種症狀卻相當罕見。家中已有一隻長期病貓福頭,我們深知及早就醫對善於隱藏病痛的貓是多麼重要,於是不敢怠慢,連忙帶查查就診。初步檢查一切無礙,但由於牠已數天不願主動進食,醫生還是建議留院輸液補充營養,靜待體能回復,順便安排更深入的檢查以確認狀況。
查查出院時,能做的檢查全都做遍了。所有報告和數據都沒有異常,但牠就是病懨懨的。我們買了各式各樣罐頭、零食,但牠還是碰都不碰,無奈之下只好開始灌食(force feed)。貓天性敏感細膩、崇尚自由,對違背其意願的事物抗拒萬分。開始時我們哄逗着餵,查查尚算能咽幾口,後來便看出牠越來越討厭灌食,眼神和叫聲都不對了,怎麼都不咽,混着口水通通吐出來。

貓幾天不吃便容易肝臟衰竭而亡,我們只好又把牠送回醫院。這次醫生決定立即為牠插鼻胃管,一天五頓輸進營養奶,等牠願意主動進食時再拆除。我們馬上添置所需裝備、物資,確保輸給查查的營養奶溫度、份量都適宜;又制定輪班輸液時間表,保證每頓間隔時間合理,也避免輸得太急或太多會引起嘔吐。一切準備就緒後,我們再次接查查出院。這次醫生欣喜地說查查一切指標均正常,是隻健康的小貓。看着牠憔悴的模樣,我只覺得這是某部超現實電影的場景,或像某個荒謬的夢。
我雖然沒受過獸醫訓練,但畢竟也是個醫者。不論人和貓在結構上是多麼不同,在中醫角度,組成一切含靈肉體的不過就是精、氣、神。何況我與查查朝夕相對近四年,如果分不出牠的狀態是好是壞,真是枉為室友。無論我用甚麼角度去看,牠其實就是「大肉已脫」的階段。理智知道該順其自然,情感上絕對不願放手。這種狀態下的主人,自然難再知行合一:一邊按時間表輸液,頓頓堅持輸足份量,對牠無力反抗只能不斷靠吐口水引吐的行為視而不見;一邊用美國獸醫的安樂死評估標準為查查計分,不忍見到牠已活得毫無樂趣,卻又欠缺勇氣承擔決定其去留的責任。思緒來回拉扯,究其根本,就是不想失去。
查查在想甚麼?我終於忍不住請能感通動物思緒的朋友幫忙。(是事實也好,是主人的安慰劑也罷。我唯一所知的便是我的無知;也因我的本行而深知現代科學的限制。我們只是幸運地生在這個科學出現並盛行不過數百年的時代,能以多一種角度了解世界的奧秘,但不代表只有這一種方法。) 朋友說,查查所願極其簡單:不打針、不插管,只願媽媽能相信牠已長大,有能力面對生命的自然循環,尊重和陪伴牠,不必再代牠抉擇一切。
一旦決定拔管,就是接受牠幾天內會離開我的事實,我是真的捨不得。自覺算是頗受眷顧的人,人生中每出現這種煎熬的時刻,很快就會得到上天提示。一天在滑YouTube,忽然出現一段臺灣醫生講述陪伴其母執行「斷食往生」的片段,最讓我深刻的一段話是「人和動物一樣,臨終前因機能減退,自然會斷食斷水,並想回到安全的地方,排清體內雜質後,便會自然離去;現代醫療的過度干預,何嘗不是剝奪了人自然死亡的權利?」那位醫生的母親,在過世前二十天不再進食、前十天不再進水,臨終前對陪伴在側的家人說「此生過得很滿足」,便撒手人寰。
即便心中已暗自決定,但還是拖得一天是一天。一個星期天,出門前為查查輸液時,牠看着我噴射式嘔吐,步伐蹣跚,連離開嘔吐物的力量也沒有。看着牠活得毫無尊嚴的樣子,我的淚水不知是不捨還是愧疚,手上卻有條不紊地為牠拔管和清潔身體。恢復自由的牠看起來輕鬆自在,馬上回到最喜愛的角落窩着睡。當天晚上,我直覺有事要發生而遲遲不睡,果然凌晨牠開始低叫,我握着牠不再粉紅的肉掌,唱着牠愛聽的童謠,感謝牠的到來和陪伴,為牠的成長和勇敢加油喝采,滿心祝福送牠離開。淚眼模糊中,我像看到牠發光的靈魂奮力衝出那無力跟上的肉身,往前去那充滿愛意的宇宙,繼續下一段有趣的旅程。

四貓之中,查查是我的心頭肉。本以為失去牠,我會如同以往每次切身經歷生死離別一樣,陷入無法自拔的憤怒悲傷甚至失能狀態,沒想到牠最後還讓我體悟到生命是如此深廣:生命之流有張有弛,臣服不代表消極;生命之圓無始無終,死亡不等於失去;生命之愛無窮無盡,思念也不必悲傷。我從未想過,生平第一次感受到自己有能力放下我執,而以對方為先、輸出無條件的愛的場景,會是在愛貓彌留時的吶喊助威。在此生我們相伴的最後,我終於放開對孻仔放不開的手,給了牠信任與尊重;牠也以乾脆利落的帥氣離場肯定我的作為。在這個失去中,我竟得到如此之多。
謹以此文獻給回歸宇宙二十五年的爸爸、九年的外公、八年的祖母和新亞同學,以及兩個月的查查。

( 文/張瑩)
注釋
[1] Wiens, J., & Cadden, C. (2011). OWS Mourning and Celebration Circle Facilitator Notes. ZENV. https://www.dropbox.com/s/w1egg5cwcwm3ajb/celebrationmourning.pdf
[2] 曹文傑博士現爲中大性別研究課程講師
[3] Kinyon, J., Lasater, I., & Stiles, J. (2015). From Conflict to Connection: Transforming Difficult Conversations into Peaceful Resolutions (pp. 240-241). Global Reach Books.
[4] Kashtan, M. (2014). Spinning Threads of Radical Aliveness: Transcending the Legacy of Separation in Our Individual Lives (pp. 167-172). Fearless Heart Publications.
[5] Kashtan, M. (2010). Wanting Fully Without Attachment. The Fearless Heart.
https://thefearlessheart.org/wp-content/uploads/2019/08/Wanting-Fully-without-Attachment.pdf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