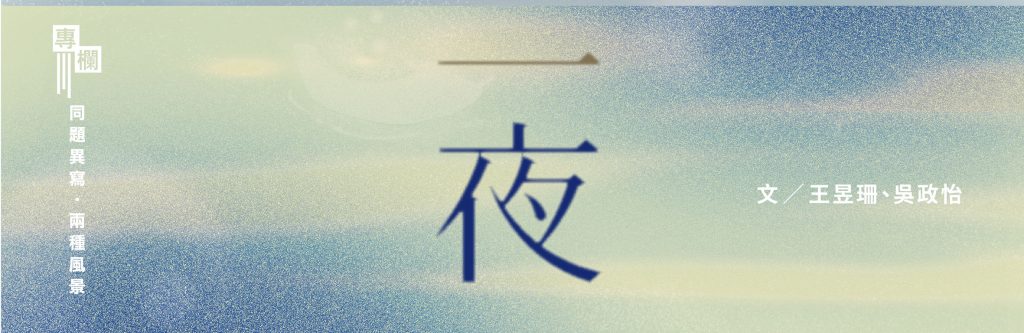
「同题异写 ‧ 两种风景」作者团队由七位背景不同的校友组成。专栏每期设一题目,由两位作者各出机杼,自由发挥。七人轮流执笔,每次不同组合,期盼刷出写作的新火花。

本期作者王昱珊(18/艺术)
于日常之间翻来覆去。主修艺术,副修中国语言及文学,毕业后与友人合租城内小小空间,延续创作寿命。喜欢窥探他人(包括自己)的生活,从中探索人的处境状态、精神情绪和关系距离。以观人的方式观世界。
天未亮便已入黑。
此处的日照消失了,刚下床就要取火点油灯。风寒,身子卷缩一团,手脚冰冷,易得病。无望地望向窗外的上空,稍有一片泛光的云也好,可惜甚么都没有。
这样的日子已维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。上一回看见日光,大概是在梦中,跟一些少年跑动在阳光照耀的青绿草坡上,汗洒闪耀出星尘。跑到草坡的一端往下看,看见一个循斜坡建造的露天圆形广场,广场上无人,座上全为虚席。青年舞动在米黄色大理石级的席间,再跳落在圆形广场中心,向耀眼的天空欢呼,回音荡漾在空中。是哪时候做的梦都已经忘了,应该是好久以前,但影像却清晰如昨日发生。
走去烧水暖身。喝一口暖流大概可以唤醒身体机能,就当是一天的起点。锌盆上的自来水喉流出一条冰柱,落在水煲中,水煲放过去烧,不久便冒出蒸气。在水煲蒸气上取暖。蒸蒸手,蒸蒸脸,蒸蒸日上,日上三竿,三竿不见影,毕竟无光。
失去日照便限制了活动时间与范围,天天不出门不见人,不算是甚么难熬的事,不过缺乏日光就缺乏动力,身体未觉累,睡意就先来报到,好像堕入了一个无限轮回时空洞,每天每夜也是同天同夜,睡的时间只是中场休息或强制注销,开眼便加载至同一数据库,数据仍然未增未减。
日复日夜复夜,在倒模的日常也想过稍为打破规律,走出家园跑个圈:握门柄推门、踏出门口、在门前踏踏几步又几步,踏出一个圆。这样的想法重重复复重重复,像被鬼压床时唤自己要呼喊出声那般,脑里彩排一千遍,念念有词却始终没有成事。
事实是外面太黑,危险。大家都这么说。自从日照消失,就连街上的路灯也无心工作,指路方向一一熄灭,前路一片漆黑未明,伸手不见指。况且,闻说黑幕处隐蔽了一些妖魔鬼怪,在不察觉的情况下就会攀附在你身上,上身难脱身。风险太多,总之不出现不在场,就不会有事故发生,家传户晓的简单道理,还是待在安全屋好。
曾经因眼疾而畏光,阳光猛烈不出门,有光的地方都要挡起来,甚至有时嫌弃天气太好。如今如所愿,终日生活在黯淡的黑盒中,疾病由眼睛转移到全身,如怕光那般怕黑。人在完全黑暗中,会本能地想办法寻光,也许连无神论者也会萌生出信仰。在抽屉里拿出一条太阳项链,戴在胸口前,踱步来回在屋的中央和窗的侧边,好快,一日就会过去,转眼一天,转眼再一天。
在坚实的黑幕里,窗口远方冒出了零星微弱的光点,出现了又消失,以为是眼睛倦怠的错觉,或者旧患复发。待在窗前再等,那细小而坚强的发光颗粒再出现、震动、闪烁。为数不多,却足以支撑整天下垂的眼帘。再看,大概三或四或五颗小的光点逐渐变大,提示着光点的距离与移动轨迹,一摆一摆的靠近过来。
在桌上抓拾过油灯,握门柄推门,踏出门口,在门前踏踏几步又几步。眼前的星光斑点更加接近,再集合成七八颗。此时的寒风对体感而言已不算甚么,另一只手尽力作为火焰的避风港,让它在风中仍能自由摆舞。光点越近,就越形成不规整的形态,舞动在空气之中,飘出一尾尾烟,照亮了掌光者的身影,一些似乎陌生又似曾相识的面貌,再围成一团温和而不可见的暖空气。静夜里无人发声,仅带着各自保有的光前来聚结,自然地引来更多光点结队,再走往下一个方向。
转过身来,原本的安全屋子埋藏在黑暗之中消失不见。没有回头路,就带着余光跟随大队,远走去一道未明的路上。
( 文 / 王昱珊 )

本期作者吴政怡(16 /中文)
曾任记者、中学教师。现为无业游民,休养生息中。最近不是在旅行, 就是在规划旅行。喜欢学习木工、瑜伽、舞蹈,让自己全神贯注,感受世界静止的瞬间。
这一夜,特别漫长,也特别短促。
妈妈把我从睡梦中拍醒,声音颤抖着:「走,医生打来叫我们去医院。」
死寂的街道上,只有晕黄的路灯挺直身子站立,邮筒、路牌和地砖都在稳稳地沉睡。巴士总站里疏落地停泊了两三辆的士,我们赶紧跳上最近的一辆,从葵盛直奔黄大仙医院。
我好像知道,又好像不知道发生了甚么事——还是不愿意知道?
赶到医院,护士把我们领到病床前:「吴先生在X时X分离世了。」父亲的双眼和嘴巴凝固在半张半合的瞬间,身体宛如动物标本,不用触碰也能「看」到是僵硬而冰冷的。
原来亲人离世并不像电视剧那样——病人家属围拢在病床前低头痛哭,声嘶力竭地喊叫:「别走啊、别走啊!你怎么舍得丢下我们啊?」「不要吓我!快醒醒!醒醒!」哀伤以缓缓淌下脸庞的眼泪呈现,以哽塞在喉头的只字词组呈现,以笼罩鼻头的酸意呈现。偏偏不是以从小到大沉迷的电视剧式情节呈现。
一夜,体验到不知如何应对的真实。
父亲的面庞,很熟悉,却又很陌生,似乎不是同一个人来的。合上眼的他,怎会没有我从小熟悉的鼻鼾声?
自个多月前,父亲证实患上肺癌末期起,便变得越来越陌生。原本经常手执「红双喜」香烟和打火机、穿T恤牛仔裤的他,突然整天躺在病床上,穿条子或格子病人服。接受治疗后,原本短小稀薄的白发变得更少,人瘦得只剩下皮包骨,神情越来越呆滞,说话行动都越来越乏力。
大概自从我六岁与父亲分睡一张「双层床」的上下铺开始,十多年来,我都没有好好睡过一觉。每次被他沉重的鼻鼾声吵得难以入睡,我就会悄悄溜起来,施展温柔的小技俩——有时是搔痒,有时是敲一敲床沿围栏,直至鼻鼾声停顿为止。理想的效果是令父亲半醒,鼻鼾声暂停却不会清醒至起床,偷得空档让我入睡。偏偏我是难入睡的体质,早在成功入睡前的空档,鼻鼾声又故态复萌的话,我只得重施故技。有时心急,用力稍猛,父亲醒了,歉疚下自己也睡不着。
这个多月的夜,他都无法入睡,无法下床「屙夜尿」,无法拿起水杯……这一夜,他终于能休息了。
处理完文件后,天空逐渐泛白,我和妈妈回到家,梳洗、睡觉,其实不记得有没有入睡,可能只是躺在床上闭着眼睛。
天亮了,眼见家里甚么都没变,但从此家里少了一个人。
人生中总有一夜历经身分转变——孩童变成人、未婚变已婚、儿女变父母。而我,则是一夜失去了父亲的孩子。那一夜,我只有十六岁。成长,来得那么猝不及防。
想起初中时读过的课文〈爸爸的花儿落了〉(节录自林海音《城南旧事》),爸爸叫英子要「闯练,闯练」,爸爸走了,英子意会到自己「不再是小孩子」。可是我连一句从父亲口中吐出的叮嘱也没有收到。最后在医院探病,他就如同平日般沉默寡言。他知道在那个晚上,生命就走到尽头吗?他估计到仍选择不说话,还是没有预想之下,怀着满腔未说的话离开?我真希望有那么两个字可以抓在手中,哪怕就只有两个字也好。现实中,即将离世的人不会很戏剧化地深呼吸最后一口气,在亲人怀中一字一顿地说遗言,甚至说完刚好断气,更多的是没有一声再见,孤独默然地消逝。
早前看了翁子光导演的《爸爸》。刘青云所饰演的爸爸,一夜之间,由人夫变成鳏夫,儿子被送进精神病院。一家人齐齐整整吃过晚饭,妻子和子女都回家休息,剩他独自守着通宵营运的餐厅,岂料数小时后警察登门告知,儿子亲手杀死妻子和小女儿的噩耗。往警署录口供后,翌日,爸爸如常开铺经营茶餐厅,如常和街坊打招呼,如常买餸,如常吃饭,如常喂猫。如此真实,看得我隐隐作痛。
失去至亲至爱,一夜白头、黯然销魂、生死相随……都是太浪漫的写法,现实中绝大部分人仍是如常过活。尽管面对家破人亡的剧变,日子也得过下去。心头被戳开巨大的空洞,时间无法填补,只能习惯。
夜,或乌云盖天、月隐星稀,或皓月当空、星光闪烁。但日出月落,黑暗过后是晨曦,周而复始,变幻无常,变幻也有时。
( 文 / 吴政怡 )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