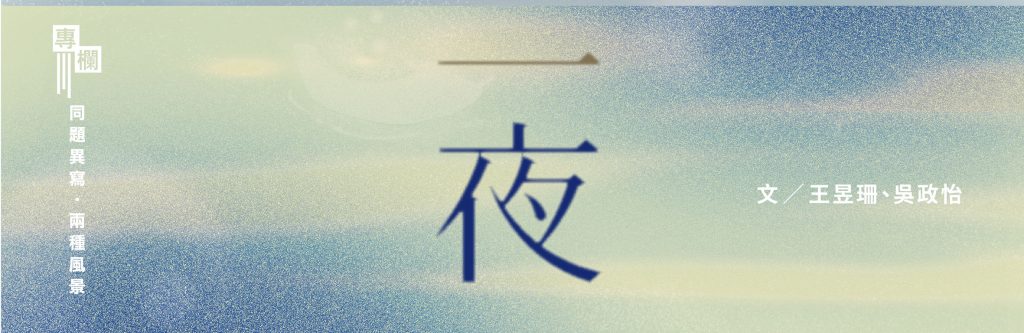
「同題異寫 ‧ 兩種風景」作者團隊由七位背景不同的校友組成。專欄每期設一題目,由兩位作者各出機杼,自由發揮。七人輪流執筆,每次不同組合,期盼刷出寫作的新火花。

本期作者王昱珊(18/藝術)
於日常之間翻來覆去。主修藝術,副修中國語言及文學,畢業後與友人合租城內小小空間,延續創作壽命。喜歡窺探他人(包括自己)的生活,從中探索人的處境狀態、精神情緒和關係距離。以觀人的方式觀世界。
天未亮便已入黑。
此處的日照消失了,剛下床就要取火點油燈。風寒,身子捲縮一團,手腳冰冷,易得病。無望地望向窗外的上空,稍有一片泛光的雲也好,可惜甚麼都沒有。
這樣的日子已維持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。上一回看見日光,大概是在夢中,跟一些少年跑動在陽光照耀的青綠草坡上,汗灑閃耀出星塵。跑到草坡的一端往下看,看見一個循斜坡建造的露天圓形廣場,廣場上無人,座上全為虛席。青年舞動在米黃色大理石級的席間,再跳落在圓形廣場中心,向耀眼的天空歡呼,回音蕩漾在空中。是哪時候做的夢都已經忘了,應該是好久以前,但影像卻清晰如昨日發生。
走去燒水暖身。喝一口暖流大概可以喚醒身體機能,就當是一天的起點。鋅盆上的自來水喉流出一條冰柱,落在水煲中,水煲放過去燒,不久便冒出蒸氣。在水煲蒸氣上取暖。蒸蒸手,蒸蒸臉,蒸蒸日上,日上三竿,三竿不見影,畢竟無光。
失去日照便限制了活動時間與範圍,天天不出門不見人,不算是甚麼難熬的事,不過缺乏日光就缺乏動力,身體未覺累,睡意就先來報到,好像墮入了一個無限輪迴時空洞,每天每夜也是同天同夜,睡的時間只是中場休息或強制登出,開眼便載入至同一數據庫,數據仍然未增未減。
日復日夜復夜,在倒模的日常也想過稍為打破規律,走出家園跑個圈:握門柄推門、踏出門口、在門前踏踏幾步又幾步,踏出一個圓。這樣的想法重重複複重重複,像被鬼壓床時喚自己要呼喊出聲那般,腦裏綵排一千遍,念念有詞卻始終沒有成事。
事實是外面太黑,危險。大家都這麼說。自從日照消失,就連街上的路燈也無心工作,指路方向一一熄滅,前路一片漆黑未明,伸手不見指。況且,聞說黑幕處隱蔽了一些妖魔鬼怪,在不察覺的情況下就會攀附在你身上,上身難脫身。風險太多,總之不出現不在場,就不會有事故發生,家傳戶曉的簡單道理,還是待在安全屋好。
曾經因眼疾而畏光,陽光猛烈不出門,有光的地方都要擋起來,甚至有時嫌棄天氣太好。如今如所願,終日生活在黯淡的黑盒中,疾病由眼睛轉移到全身,如怕光那般怕黑。人在完全黑暗中,會本能地想辦法尋光,也許連無神論者也會萌生出信仰。在抽屜裏拿出一條太陽項鏈,戴在胸口前,踱步來回在屋的中央和窗的側邊,好快,一日就會過去,轉眼一天,轉眼再一天。
在堅實的黑幕裏,窗口遠方冒出了零星微弱的光點,出現了又消失,以為是眼睛倦怠的錯覺,或者舊患復發。待在窗前再等,那細小而堅強的發光顆粒再出現、震動、閃爍。為數不多,卻足以支撐整天下垂的眼簾。再看,大概三或四或五顆小的光點逐漸變大,提示着光點的距離與移動軌迹,一擺一擺的靠近過來。
在桌上抓拾過油燈,握門柄推門,踏出門口,在門前踏踏幾步又幾步。眼前的星光斑點更加接近,再集合成七八顆。此時的寒風對體感而言已不算甚麼,另一隻手盡力作為火焰的避風港,讓它在風中仍能自由擺舞。光點越近,就越形成不規整的形態,舞動在空氣之中,飄出一尾尾煙,照亮了掌光者的身影,一些似乎陌生又似曾相識的面貌,再圍成一團温和而不可見的暖空氣。靜夜裏無人發聲,僅帶着各自保有的光前來聚結,自然地引來更多光點結隊,再走往下一個方向。
轉過身來,原本的安全屋子埋藏在黑暗之中消失不見。沒有回頭路,就帶着餘光跟隨大隊,遠走去一道未明的路上。
( 文 / 王昱珊 )

本期作者吳政怡(16 /中文)
曾任記者、中學教師。現為無業遊民,休養生息中。最近不是在旅行, 就是在規劃旅行。喜歡學習木工、瑜伽、舞蹈,讓自己全神貫注,感受世界靜止的瞬間。
這一夜,特別漫長,也特別短促。
媽媽把我從睡夢中拍醒,聲音顫抖着:「走,醫生打來叫我們去醫院。」
死寂的街道上,只有暈黃的路燈挺直身子站立,郵筒、路牌和地磚都在穩穩地沉睡。巴士總站裏疏落地停泊了兩三輛的士,我們趕緊跳上最近的一輛,從葵盛直奔黃大仙醫院。
我好像知道,又好像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——還是不願意知道?
趕到醫院,護士把我們領到病床前:「吳先生在X時X分離世了。」父親的雙眼和嘴巴凝固在半張半合的瞬間,身體宛如動物標本,不用觸碰也能「看」到是僵硬而冰冷的。
原來親人離世並不像電視劇那樣——病人家屬圍攏在病床前低頭痛哭,聲嘶力竭地喊叫:「別走啊、別走啊!你怎麼捨得丟下我們啊?」「不要嚇我!快醒醒!醒醒!」哀傷以緩緩淌下臉龐的眼淚呈現,以哽塞在喉頭的隻字片語呈現,以籠罩鼻頭的酸意呈現。偏偏不是以從小到大沉迷的電視劇式情節呈現。
一夜,體驗到不知如何應對的真實。
父親的面龐,很熟悉,卻又很陌生,似乎不是同一個人來的。合上眼的他,怎會沒有我從小熟悉的鼻鼾聲?
自個多月前,父親證實患上肺癌末期起,便變得越來越陌生。原本經常手執「紅雙喜」香煙和打火機、穿T恤牛仔褲的他,突然整天躺在病床上,穿條子或格子病人服。接受治療後,原本短小稀薄的白髮變得更少,人瘦得只剩下皮包骨,神情越來越呆滯,說話行動都越來越乏力。
大概自從我六歲與父親分睡一張「碌架床」的上下鋪開始,十多年來,我都沒有好好睡過一覺。每次被他沉重的鼻鼾聲吵得難以入睡,我就會悄悄溜起來,施展温柔的小技倆——有時是搔癢,有時是敲一敲床沿圍欄,直至鼻鼾聲停頓為止。理想的效果是令父親半醒,鼻鼾聲暫停卻不會清醒至起床,偷得空檔讓我入睡。偏偏我是難入睡的體質,早在成功入睡前的空檔,鼻鼾聲又故態復萌的話,我只得重施故技。有時心急,用力稍猛,父親醒了,歉疚下自己也睡不着。
這個多月的夜,他都無法入睡,無法下床「屙夜尿」,無法拿起水杯……這一夜,他終於能休息了。
處理完文件後,天空逐漸泛白,我和媽媽回到家,梳洗、睡覺,其實不記得有沒有入睡,可能只是躺在床上閉着眼睛。
天亮了,眼見家裏甚麼都沒變,但從此家裏少了一個人。
人生中總有一夜歷經身分轉變——孩童變成人、未婚變已婚、兒女變父母。而我,則是一夜失去了父親的孩子。那一夜,我只有十六歲。成長,來得那麼猝不及防。
想起初中時讀過的課文〈爸爸的花兒落了〉(節錄自林海音《城南舊事》),爸爸叫英子要「闖練,闖練」,爸爸走了,英子意會到自己「不再是小孩子」。可是我連一句從父親口中吐出的叮囑也沒有收到。最後在醫院探病,他就如同平日般沉默寡言。他知道在那個晚上,生命就走到盡頭嗎?他估計到仍選擇不說話,還是沒有預想之下,懷着滿腔未說的話離開?我真希望有那麼兩個字可以抓在手中,哪怕就只有兩個字也好。現實中,即將離世的人不會很戲劇化地深呼吸最後一口氣,在親人懷中一字一頓地說遺言,甚至說完剛好斷氣,更多的是沒有一聲再見,孤獨默然地消逝。
早前看了翁子光導演的《爸爸》。劉青雲所飾演的爸爸,一夜之間,由人夫變成鰥夫,兒子被送進精神病院。一家人齊齊整整吃過晚飯,妻子和子女都回家休息,剩他獨自守着通宵營運的餐廳,豈料數小時後警察登門告知,兒子親手殺死妻子和小女兒的噩耗。往警署錄口供後,翌日,爸爸如常開舖經營茶餐廳,如常和街坊打招呼,如常買餸,如常吃飯,如常餵貓。如此真實,看得我隱隱作痛。
失去至親至愛,一夜白頭、黯然銷魂、生死相隨……都是太浪漫的寫法,現實中絕大部分人仍是如常過活。儘管面對家破人亡的劇變,日子也得過下去。心頭被戳開巨大的空洞,時間無法填補,只能習慣。
夜,或烏雲蓋天、月隱星稀,或皓月當空、星光閃爍。但日出月落,黑暗過後是晨曦,周而復始,變幻無常,變幻也有時。
(文/吳政怡)

